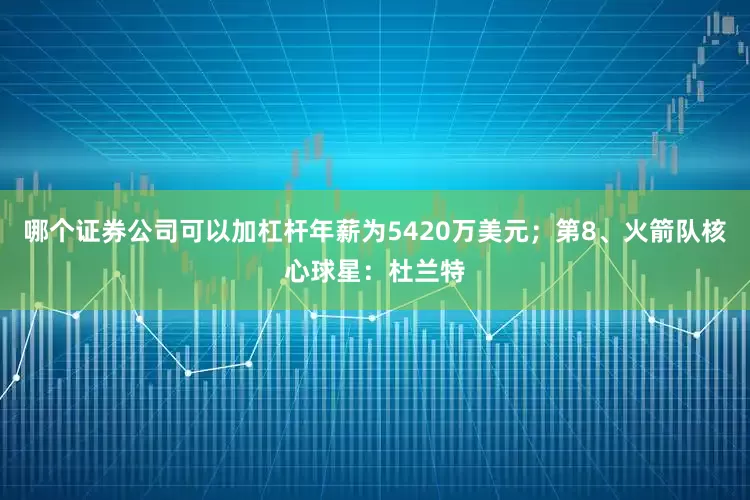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一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作家。
他研读《道德经》,热爱李白,用筷子吃饭,还有杨炼、西川等中国诗人朋友,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克普桑尼也是一个能说中文的汉学家。
2002年,拉斯洛来华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2004年,他将此次中国行的旅途见闻及访谈写成纪实性非虚构作品出版,后被译为英文,这算是拉斯洛唯一一部非虚构纪实文学作品。
在匈牙利语原版中,主角名为László Dante(拉斯洛·但丁),与写《神曲》的14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同名。在英文版中,拉斯洛把名字改成了László Stein(拉斯洛·斯坦因),与匈牙利裔英国考古学家Marc Aurel Stein(马尔克·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同名,而斯坦因曾把大量敦煌文物运回欧洲。
展开剩余89%拉斯洛貌似也想像斯坦因一样,在中国寻得一些什么然后如获至宝地带回。他要找什么?
2009年11月12日,拉斯洛在北京 图据:视觉中国
壹
1991年,拉斯洛曾以记者身份第一次来华访问,从此深深迷恋上中国。不仅称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人文博物馆”,回国后更会在家里听京剧、出门吃饭尽量找中餐。
出于对李白的偏爱,1998年5月拉斯洛再度来华时复刻了李白的足迹。在译者余泽民陪同下,两人从北京出发一路走过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等城市,又在重庆上船途经三峡而至武汉。
回匈牙利后,拉斯洛将此次中国行写成一篇散文体长篇游记《只有漫天星辰的天空》。
奉节夔门,李白有名篇《早发白帝城》 图据:视觉中国
四年后的2002年5月,拉斯洛从南京出发开始了又一次中国行。这次与他同行、充当翻译的是一名在上海读书的欧洲大学生,他们乘坐火车、公交车和出租车,开始了在长江三角洲的游历。
拉斯洛去了九华山、普陀山和天台山的古寺,去了扬州、镇江、周庄、杭州、绍兴、宁波和苏州。他既在长江以南的“传统高雅文化中心城市”中穿梭,也在百多年前才开始兴起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停驻。
安徽池州九华山化城寺。拉斯洛离开南京后的第一站 图据:视觉中国
用拉斯洛自己的话说,他计划要找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遗迹”。杨炼曾经告诉他,“中国最初的精神在某个地方的深处活着”,所以拉斯洛要找的是“珍贵的中国古典文化秩序中可能仍然幸存的东西”。
贰
在1985年发表处女作《撒旦探戈》之后,拉斯洛首次离开匈牙利,前往当时联邦德国的西柏林旅居一年。苏联解体后,他开始在世界各地游历:日本、美国和欧洲全境。拉斯洛想在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寻获一剂良方,以对抗欧美物质至上的消费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拉斯洛希望在中国能寻获心目中的理想国——毕竟世界上具备源远流长文明、在现世潮流裹挟下能不被轻易同化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但是,有过落后就要挨打记忆的中国,那时还不会像现在这样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在南京,“灵谷寺的这小小残片矗立在那里,在建立在一堆废墟之上的摇摇欲坠的现代化之中,就像一个小孩在黄昏的战场上,而他周围的人都死了。”
在镇江,“金山寺里有一个游乐场,里面的一切都是塑料做的,从白雪公主到唐老鸭。”
如今的金山寺,游乐场已消失 图据:视觉中国
在周庄,“早上八点开始,第一辆大巴从公路上开过来,成百上千的旅游团像一支军队一样无情地到来,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他们占据了明末清初的时代。”
显然,当异域旅行者刻意去寻获他的目标时,一切与目标不符不和谐的场景都会显得刺眼。当这些以往在别处司空见惯的场景在拉斯洛眼前浮现,他只想要迅速逃离。
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拉斯洛走进方丈的办公室,他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游客信徒们被鼓励把钱扔进募捐箱……”
位于东京的日本天台宗主寺宽永寺,日本天台宗来自于中国 图据:视觉中国
拉斯洛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回应。
回到北京,拉斯洛对他的诗人朋友唐晓渡倾诉,说虽然他一直告诉人们,他1998年来中国是寻找李白,其实那时他脑子里想的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化。
当然,那次旅程他最终还是收获了一些东西,他这样表述:
“我头顶上的云朵、和李白以及所有中国古典诗歌和所有中国传统头顶上的云朵,是同一片天空,仅仅知道那是同一片天空,我就充满了幸福。只是现在我感到如此不确定,以至于将信任寄托在亲爱的朋友晓渡身上,愿他现在告诉我:这里的天堂之下是否仍然是相同的(Are the heavens here above them still the same)?”
唐晓渡过了很久才回答,而且一直没有看拉斯洛,“不,它们不一样了。”
叁
类似的表达,一百年前鲁迅已经有过。
1924年暑假,鲁迅到西安讲学,顺便为他写杨贵妃的长篇小说作实地考察。十年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感叹:“……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2002年,拉斯洛曾去过鲁迅故居和三味书屋 图据:视觉中国
拉斯洛对中国古典文明的热爱,甚至在相当数量的国人之上。如果他知道鲁迅有类似表达,不知道会不会释然一些。只是越失望表明越怀希望,越执着意味着越是在意。因此拉斯洛往往冒着被视为粗鲁无礼的风险,直言不讳甚至是略带冒犯地向他所访谈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袒露他的困惑、疑问、气忿及期待,他常常寻根究底,他总是追问不休,他希望在离开中国之前得到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
面对拉斯洛,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思考角度出发来回答,而其中往往不乏真知灼见。
杨炼的父亲杨清华,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他告诉拉斯洛:“(中国文化)是一种建立在书写绝对优先地位之上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在书面语言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书写对中华民族始终至关重要。这一传统与语言息息相关……每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过去和现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欧阳江河认为:“欧洲人认为文化如同博物馆里的文物,是可掌握、可触摸的东西。而对中国人来说则完全不同,文化的精髓只有通过精神的形式才能得以保存……中国文化的精髓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只有通过文字才能理解。”
诗人欧阳江河 图据:视觉中国
诗人小海答他:“古典文化……只有体现在某个人身上,才真正成为文化。”
在大学教授文学的姚鲁人则指出拉斯洛的先天不足,“(要了解中国古典文明)你得在这里生活,你得了解中国人的生活。还有一件事:你不懂汉字。中国文化的基础是汉字。(如果不懂汉字)你永远不会对中国文化有任何深入的了解。”
……
诗意的栖居在于超越现世。陶渊明并没有打造一座桃花源让后代可以凭吊古迹,他只是用寥寥数百字,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各自心里建起各自的桃源来。
不知道拉斯洛从回答中收获了多少。
结束中国之行前,他在苏州网师园与一位名为Wu Xiaohui的园林专家见面后,似乎找到了答案。Wu在纸上写下老子的名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送给拉斯洛,不懂中文的拉斯洛似乎有悟于心。
拉斯洛用匈牙利语向Wu兴奋地表示,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但他已经听懂了、完全听懂了、每个字都听得懂……他不会忘记网师园,不会忘记阳光洒在爬满藤蔓的墙上,不会忘记这一刻鸟儿的啁啾,不会忘记围坐在这张桌子旁的人,不会忘记龙井茶的香气和味道,也永远不会忘记Wu的话和他写下的东西。
2002年时的拉斯洛 图据:视觉中国
二十多年过去,拉斯洛当年提出的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却仍然没有过时,在当下仍然值得思考。只是拉斯洛来华时中国刚刚加入WTO不到半年,如今早已不同往日。一个亘古以来经历数千年始终不断、在世上独一无二的文明,也自然有其特异的生命力。
对于不谙中文的拉斯洛而言,他那时甚至料想不到二十多年后会拿诺奖,几千年的特异或许也超出了他所能意料的边界。
发布于:四川省配资炒股首选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